当主流题材挤满银幕时,张家辉想给观众多一个非主流的选择。时隔6年再做导演,他又拍了一部心理惊悚电影——《赎梦》。
从《盂兰神功》《陀地驱魔人》再到《赎梦》,张家辉的导演作品几乎清一色地走非主流市场路线。用他的话来说,既然主流的路有很多人走了,为什么不走一条没那么多人走的路呢?这样还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选择。
张家辉做导演有个习惯,他喜欢自己编剧。构思本子的时候,他其实也想过找编剧来写。但常常碰到的情况是,编剧会来“质问”他,“要抄哪一部戏?想好抄哪部戏,我才能帮你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如果要抄,我就不需要找你啦!但他们都跟我说,你不说你想抄哪一部,我不能帮你写的。结果就变成我自己写了。”

至今写了四部电影的张家辉,创作灵感基本都来自新闻、访问、漫画或者纪录片。
他说做导演压力很大,什么都跟自己有关。做演员就轻松了,拍完就走,很多事情都不用管。
“当导演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人拍我想拍的故事。如果有导演找我演有突破的角色,我立马不做导演了。但演员,我一定是会继续做的。”
《赎梦》上映之前,时光网与张家辉完成了一次深度对话。
镜头前的他语速不快,眼神却很笃定。除了表演经历,他还聊起让他崇拜至极的杜琪峰、助力他二度“封帝”的林超贤、早期赏识他的邱礼涛、给了他很多机会的王晶、以及令人怀念的陈木胜......他说自己在他们身上汲取了无数养分,这些导演让他受益匪浅。导演他可以不做,但演员他一定会当下去。

张家辉是个爱做梦的人。他对 “梦” 带着一份敬畏。“梦是藏在心里的压力、白天不敢想,晚上会自己跑出来。”他会刻意记住梦里的异常感受:“有时候知道自己在做梦,就会盯着那些不对劲的细节看,醒了赶紧记下来。” 这些细碎的体验,后来成了《赎梦》的素材。
聊起新片《赎梦》,张家辉反复强调这不是一部晦涩的艺术片,“是用大量梦境包装的商业娱乐片,有很实在的故事线。”灵感源于一部关于“睡眠瘫痪症” 的纪录片。“睡眠瘫痪症”就是中国人说的“鬼压床”。作为导演,他意识到“鬼压床”这种现象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新鲜的切口。于是他把现实的素材藏在梦境里,用心理惊悚的外壳包裹起一个非常规题材的故事。张家辉坦言想拍点不一样的东西。当主流题材挤满银幕时,想给观众多一个非主流的选择。

为了让故事落地,他没少下功夫。自编自导是他做导演的习惯。剧本由他亲自执笔。过去执导的作品都有他编剧的身影。他说,他也曾想过找编剧帮写故事。但编剧们总是问他:“你想抄哪部戏?说出来我才能帮你写。” 他哭笑不得:“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如果要抄,我就不需要找你啦!但他们都说,不说想抄哪一部,就不能写。结果就变成我自己写了。”
他想探讨更实在的东西:原生家庭、因果报应,还有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他在《赎梦》加了很多商业元素,梦境的冲击、紧凑的节奏,都是为了让观众看得进去。“非主流题材”的创作藏着他的固执:“大家都拍主流,我就想试试别的。但前提是,观众看得懂,得喜欢。”
蔡辛强是《赎梦》里最复杂的角色。前半生风光,后因妻子在金融市场的冒进跌入深渊,为了脱困犯下致命大错。张家辉用三个词形容他:“可悲,可怜,可爱。”“他和老婆能共富贵,也能共患难,到最后都没分开,这一点很浪漫。” 但这份浪漫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碾压。
为了填补自家债务,他骗取了好友的巨额财富,导致好友家破人亡。悲惨故事发生的那一年,恰好是2008年,正值金融风暴席卷香港。“那时候很惨,三两天就有人轻生,甚至全家出事。” 张家辉见过风暴下的众生相,但他没直接把这些拍出来,而是把绝望揉进了角色的骨血里。蔡辛强苦陷泥潭,好友全家离世,他们的每一次挣扎,都是对时代创伤的回望。

《赎梦》路演时,有观众问张家辉:“蔡辛强骗人的选择是无可奈何吗?” 他摇头,“再难也不能害人。哪怕破产、坐牢、干粗活,都比伤天害理强。” 说这话时,张家辉相当于给这个角色定了调。蔡辛强的“悲剧感”来自他的 “不彻底”。他不是纯粹的好人,也不是绝对的坏人,只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而像很多人一样,走着走着,他忘了一开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赎梦》的片场,张家辉有两个身份。有时他站在监视器后,对着对讲机喊 “卡”,这是导演张家辉;有时他换上角色的装扮,瞬间成了在生活里跌撞的蔡辛强,这是演员张家辉。
“为什么非要自己下场演?”“因为电影说到底是给观众看的商品。”演员张家辉还是在业内活跃的演员,导演张家辉没道理放着不用。
张家辉舍不得《赎梦》这个故事,蔡辛强身上那股拧巴劲儿,他想亲自诠释。写剧本时,他其实已经在心里把每个角色都“演”一遍,连语气和动作都想得很清楚。这份对角色的理解,让他既能指导表演,也能在上场时迅速入戏。
他笑言当导演太累了,演员拍完就能走,但导演要扛到最后,骂名掌声都得接,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拿起了导筒。“我当导演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人拍我想拍的故事。如果有导演找我演有突破的角色,我立马不做导演了。但演员,我一定是会继续做的。”

回望张家辉的电影路,连着一串响当当的伯乐姓名:邱礼涛、王晶、林超贤、杜琪峰、陈木胜......一个个鼎鼎有名的导演如明镜,照出了他骨子里的可能性,推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90年代中期,张家辉活跃在银幕,王晶是其中一个为他打开电影大门的导演。《赌侠 1999》和《赌侠大战拉斯维加斯》里吊儿郎当、插科打诨的化骨龙,《千王之王 2000》里神经兮兮的梁宽......
“搞笑的、严肃的、神经病的、老千的…… 他让我演了太多不一样的角色。”那些现在看来略显青涩的人物,让彼时的张家辉成为了备受欢迎的“喜剧配角”。说起长期合作的王晶,张家辉眼里仍有感激:“他让我演了很多类型的电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邱礼涛也是比较早欣赏我的导演,让我去拍一些比较有发挥的影片。”2006 年的《黑白道》,张家辉演卧底探员海生。
那个角色藏着太多秘密,眼神里一半是警察的正义,一半是卧底的挣扎,连抽烟的姿势都带着一股劲儿。和他过往在赌片里插科打诨的形象判若两人。
在邱礼涛的镜头下,张家辉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灵魂。如今两人虽不常合作,却还会约着聚会,“他还是老样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敏捷的东西。”

提到林超贤,张家辉语气里带着点骄傲。俩人合作过《证人》《线人》《激战》等多部作品。“都能明白对方的用意,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相互配合,我们是最佳拍档啊。”
张家辉凭借林超贤的电影拿过两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可比起奖杯,他更念着与林超贤那份独特的默契。他说林超贤像个电影教授,藏着很多创作心得,不随便跟别人讲,但他都知道。

杜琪峰在张家辉眼里则是“神一样的存在”。“你看《天若有情》,华仔抄起垃圾桶砸破玻璃橱窗,抢出礼服就跑,我小时候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在想,‘哇,怎么这么浪漫的事都想得出来啊?’还有《夺命金》里姜皓文受伤后浑身是血,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好像再等一秒搭档就能把钱带回来。 张家辉说话时像个小粉丝,他说这种劲儿只有杜琪峰能拍出来。
他自己也撞过杜琪峰的“神来之笔”。
拍《放逐》时,张家辉刚拍完自己的戏份,回家剪了个新发型,第二天闲着没事去剧组探班。刚准备离开时,就被杜琪峰喊住回去化妆。”“化什么妆?” 他懵了。“昨天车上那段,补个镜头。”没有剧本,但杜琪峰态度坚决。“可我头发换了啊!”“不要紧。”张家辉就这样穿着新换的衣服,顶着新剪的发型,回到车里。
那段戏讲的是一场激烈械斗离场,受了重伤的张家辉回光返照,坐在车后座的吴镇宇和林雪把满身是血的他护在中间,无奈地问:“现在去哪里啊?”眼见好友身负重伤,疲惫的他们都束手无策。只剩下张家辉无力地嘟囔一句:“回家吧。” 然后慢慢地歪头靠在吴镇宇肩上,永远没了声息。
那场在被临时叫去拍的戏,成就了张家辉眼中“最杜琪峰”的瞬间。

最后说到陈木胜,张家辉的突然声音低了下去。俩人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扫毒》已经过去12年了。陈木胜走后,他无比怀念这位挚友。“
他是香港很有标志性的导演,那么年轻,那么多想法,就这么走了......”他叹了口气,很心疼,感慨香港电影又少了一员大将。
这些导演,各有各脾气,各有各本事。他们把张家辉这块料,磨成了现在的样子。
《扫毒》中张子伟,生性随和,重情重义,在性格倔强的马昊天(刘青云 饰)和苏建秋(古天乐 饰)之间充当和事佬的角色。
因为一次失败的办案经历,与两兄弟心生隔阂,最终沦为了“毒贩”。三兄弟那些带着棱角的片段过了十几年,仍在观众的记忆里没有磨灭。
“耶稣也留不住你嘛”张家辉知道大家还在玩这个梗,自己也开始打趣起来。另一处被反复提起的场景更具张力。
电影中,张家辉与古天乐、刘青云久别重逢,站在两人面前,他声音发颤地质问刘青云:“三年了,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为什么选择他,不选择我?”
话到此处,他又开起玩笑:“这道题没得选。换作是我站在刘青云那个位置,真的很难选。”他甚至脑补了后续:“我大概会说,你别杀他们俩,我自己跳下去算了。”

《扫毒》提名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却没为张家辉带来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帮助张家辉两度站上金像奖影帝领奖台的电影,一部是《证人》,另一部是《激战》。
2009年的《证人》里,他演一个偏执的绑匪。为了立住这个角色,他瘦到脱形,眼神里淬着狠劲,仿佛随时能透出刀光。“那时候就一个念头,必须让观众相信,我就是那个人。”
《证人》为他带来了首座金像影帝奖座。奖项揭晓时,张家辉紧紧抱着身旁的妻子关咏荷,然后又一一与幕后团队拥抱,再快步登台接受荣誉和掌声。这个奖他等了太久了。那一年,张家辉45岁。手捧奖座的他在台上手舞足蹈,希望大家能记住他那一刻的模样。

荣誉从不是他的停驻点 他说人总想着往前看,不会因为别人夸几句,就赖在叫好声里不走。后来拍《激战》,他为了练出贴合角色的肌肉,每天举铁到手上结满厚茧,甚至断了手指也没停。他说《激战》比《证人》更“难忘”:“不光是受伤、拿奖,更因为好多人说,看完想去健身,想为生活拼一次。观众的反应是空前的。这也是我很难忘的一部作品。”
被需要的感觉在他心里比奖杯更沉。《激战》后,他演过杀手、催眠师,精神病人。在不同角色体验过千百种人生,也拿遍了大大小小的奖项,“成功不敢说,但我希望自己还在尝试。”

说到导演这个身份,张家辉倒很坦诚:“其实没什么野心,没非要逼着自己去做,以后不做导演也没关系。但要说不当演员,可能真的很难,还有太多角色没试过,太多人生没体验过。”
这或许就是张家辉人生的答案,导演是可选项,演员是必选项。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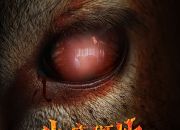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