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数智时代建构电影知识体系尤其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需要在跨界融通的数智思维与多模态、全感知和强交互的电影思维基础上,通过拓展电影研究边界、革新电影研究范式与推动电影知识生产,增进学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完成人工智能驱动的思维跃迁,并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整体思维观,跨越中外、古今、史论与知行的界限,在主客交互、道器并重、物我混融与人机共生的层面重构电影研究。
关键词: 知识体系 电影研究 人工智能 数智思维 电影思维 学科实践
迄今为止,电影研究不仅可以被当作一种横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和媒体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学科界限的学术领域,而且已经成为一门研究电影作为思想容器、艺术形式、传播媒介与文化载体,并涵盖电影生产与消费、电影历史与理论,以及电影批评与实践等各个环节的学科专业。随着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电影”概念本身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电影研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也迎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与电影思维的跨界融通,也将成为“重构”电影研究必然面对且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
从“重建”到“重构”:
电影研究的论域转换
在欧美或英语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一门学科专业的“电影研究”(film studies或cinema studies),便逐渐获得了在教学、科研与公共交往、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合法性,并出版印行了大量以“电影研究”为主题的各种词典、教材、导论、指南、期刊和著作。到目前为止,开设“电影研究”“电影与媒体研究”等相关院系和专业的教育机构也越来越多。仅就美国而言,即有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匹兹堡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等数十所著名大学,已经在“电影研究”和“电影与媒体研究”等领域,逐渐形成各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科研体系。
相较而言,中国学界对“电影研究”的认知起步较晚,甚至迟至千禧年之后才初见规模;除了对欧美尤其英语学界的“电影研究”相关成果予以针对性的转译和阐发之外,大多聚焦于电影产业、动画电影、微电影、科幻电影和电影改编等应用性的、相对“热门”的研究领域,或有关电影艺术与电影美学的概论、原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电影理论、电影史与电影批评,往往缺乏将“电影研究”作为学科专业予以整体观照的主体意识,也没有在对电影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理论和方法的持续探索中,逐渐形成相应的主题性论域或架构性知识体系。跟欧美等地的教育机构相比,除了在专业的电影学院、传媒学院与综合大学植入一般性的电影研究课程以外,中国大学仍未专门开设以“电影研究”或“电影与媒体研究”等命名的相关院系和专业。
基于2025年5月28日中国知网总库,以“电影研究”为篇名展开中文/外文搜索,通过总体趋势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果。参见图1-3:
显然,在全球学术语境里,以英语发表的“电影研究”成果数量占据50%以上的份额,而中文只占1%;在中文学术语境里,1937—1949年以及1966—1978年间的“电影研究”,也几乎为空白,只是从2003年中国电影真正进入产业化时代以来,成果数量才开始显著攀升。中文“电影研究”关注的主要主题,确实大多为更具应用性和实用性特征的“热门”议题,暂未形成中文电影研究的特定路径和内在逻辑。
实际上,欧美或英语学界的“电影研究”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学科框架,也总体保持着批判性的、动态更新的开放气质。在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的《电影研究:关键概念》1一书中,便全面涵盖了各种电影类型、运动、理论和制作术语,第四版还新增了计算机生成图像、媒介融合、邪典电影、数字电影、后数字电影、道格玛95、运动—影像、时间—影像、配额电影、3D技术等“关键概念”;同样,作为一部关于电影研究的参考著作,《牛津电影研究词典》2也通过对“电影研究”学科的全面调查,以对该领域的“系统概述”和“综合地图”为基础,讨论了电影研究的历史及其教学和研究现状,并详细介绍了电影的历史、理论和制作,包括电影的类型和运动,各个国家的电影及电影关键技术术语,如作者、作者论、数字电影、电影理论、类型、哲学和电影、现实主义、无声电影、3D电影等等;另外,作为一部专为电影专业准备的综合教材,吉尔·内尔姆斯(Jill Nelmes)主编的《电影研究导论》3一书,也主要引导学生了解“电影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和主要概念,追溯电影的发展历史,并介绍了一些主要国家的电影状况,还有电影制作的工业背景、当代电影技术、电影形式和叙事、受众与反应、电影创作与电影作者、明星研究、电影类型研究、纪录片形式、动画语言、性别与电影、非洲侨民电影、英国电影、印度电影、拉丁美洲电影、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蒙太奇电影等等。正如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为该书撰写的“前言”所示,《电影研究导论》应对了“如何讲述一门学科和一种媒介的故事”的挑战,并将作为一门“学科”的“电影研究”和作为一种“实践”的“电影制作”结合在一起,全面考察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电影的“广度”和“深度”。
与此相应,欧美各大学电影研究、电影与媒体研究等院系和专业的培养目标、学习方向与核心课程等,也大约遵循这一“学科”和“实践”、“广度”和“深度”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官网信息,南加州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系开设学士、硕士和博士项目,“提供深入的媒体和娱乐知识,服务于未来的媒体制作人和学者”4,其课程体系中,涵盖电影与媒体创作、制作、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所需的文化、艺术、政治和商业背景,关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文化、历史和叙事结构,学生将获得在不断发展的电影与传媒行业中所需的学术基础,并掌握在各个领域工作所需的广泛的工具和知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电影与媒体研究项目,也定位于“真正的行业教育,培养对历史上和现代的电影与媒体的批判性理解”5,旨在帮助学生亲身体验电影与媒体的制作过程,了解电影与媒体的历史并进行批判性思考,还将让学生建立坚实的人文学科背景。为此,学生需要全面了解动态影像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以及电影与各学科之间的相关性,需要熟悉电影的主流叙事、默片、先锋派、纪录片、动画片和实验电影及媒体等各种形式,熟练运用批评和分析技能撰写论文并能提出原创性论点,需要熟悉电影制作创意方面的核心技能,以及通过各种美学、文化、历史和理论框架对电影进行解读的能力等等。
当然,多样化建构的动态过程,也意味着“电影研究”不断“解构”或“重建”的过程。本文的“重构”电影研究一说,主要来自大卫·波德维尔与诺埃尔·卡罗尔(Nöel Carroll)等合编的《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一书。在该书“前言”里,编者明确指出,贯穿全书的任务是引介“电影研究”的“新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打破和扬弃数十年积淀的教条,更新“批判性思考”的精神。在编者看来,“我们称之为大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理论在英美电影研究中大行其道。大理论著名的化身是由各种学说规则构成的聚合体,这些清规戒律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及各种变异了的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大理论被提高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以供人们去理解所有的电影现象”6。编者坚信,“大写理论”之后最富于成果的工作将表现为“多元的理论”和“理论化”,以及出于“问题驱动”的研究和“中间层面”的学术研究,还表现为有责任感的、富于想象性的、生动活泼的研讨。编者许诺,如果追循这种构想,就能“重建”电影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卫·波德维尔与诺埃尔·卡罗尔的观念里,打破了“大写理论”或“宏大理论”的教条并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电影理论”或“电影研究”,作为一种基于“电影理论”的反思和批判而展开的创新的“电影研究”或“后理论”建构,尽管是“重建”电影研究多种路径中的一种路径,并且因将认知科学应用于电影的电影研究而在电影研究领域获得了强势地位,为电影研究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却也在此后引发了更加强烈的讨论和争鸣。本文以“重构”电影研究一说替代“重建”电影研究,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
在《数字时代中国电影研究的主要趋势与拓展路径》(2020)7、《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新路径》(2020)8、《银幕的在场与生命的庄严——媒介更迭时代重析电影本体的理论尝试》(2022)9等论文与《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2023)10、《电影史三体》(2024)11等著作里,笔者曾经对“后理论”“后电影”以及数字人文和媒介更迭时代的电影研究,进行过较为集中的思考。然而,如果结合数智时代正在呈现的跨界学术或“泛在学术”状况,将电影作为一种“绝对不纯”(阿兰·巴迪欧语)12的艺术予以观照,并将“电影研究”理解为对电影、运动影像或总体屏幕等“家族相似性”(维特根斯坦)的研究的话,“重构”电影研究至少需要在“重建”电影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面对或重新思考以下三个方面的议题:
第一,拓展电影研究边界,即在经典电影研究以及“后理论”“后电影”“后人类电影”等陆续登场的当下语境里,通过对“如何思考电影?”“什么是电影?”“电影研究何为?”的进一步发问,探讨如何将电影研究的学科实践整合在一起。
第二,革新电影研究范式,即在理论本身和电影理论均已陷入困局的“后学”状况下,结合人工智能驱动的思维跃迁,反思并重建电影哲学、电影美学、电影学与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电影体制和机制、电影生产和消费等的相互关系。
第三,以多模态、全感知和强交互的电影思维,结合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整体思维观,为电影研究带来创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并以跨界融通的数智思维重构数智时代的电影研究,为电影知识体系尤其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建设寻找突破的契机。
思维跃迁与电影研究学科实践的
广度和深度
确实,在数智时代建构电影知识体系尤其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需要在“后理论”“后电影”“后人类电影”等陆续登场的当下语境里,在多模态、全感知和强交互的电影思维与跨界融通的数智思维基础上,通过拓展电影研究边界、革新电影研究范式与推动电影知识生产,完成人工智能驱动的思维跃迁。
这也是在充分正视电影研究的学科性和实践性基础之上,为拓展电影学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而展开的一种研究路径,既指向电影学科的核心概念、相应的跨学科概念及其丰富多样的思想文化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又兼具与此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特征。
诚然,在“后理论”“后电影”以至“后人类电影”等出现之前,包括亨利·柏格森、贝拉·巴拉兹、瓦尔特·本雅明、鲁道夫·爱因汉姆、谢尔盖·爱森斯坦等在内的思想家和电影人,为电影研究所作的贡献,无疑仍具重要的启示意义,期待着研究者不断“重返”。尤其安德烈·巴赞对“电影是什么”的追问及其留下的丰厚遗产,也始终是后来的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参照系或出发点。同样,在“后理论”“后电影”以至“后人类电影”等出现之际或影响之后,包括海德格尔、米歇尔·福柯、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吉尔·德勒兹、贝尔纳·斯蒂格勒、让·吕克-戈达尔、大卫·罗德维克、马文·明斯基等在内的哲学家、电影人和科学家,及其在技术哲学、知识/媒介/电影考古学、新媒体理论、情感哲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诸多思想和观念,对于拓展电影研究边界、革新电影研究范式和推动电影知识生产进而“重构”电影研究,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如此,研究边界的拓展、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学科实践的深广度,依然主要取决于研究主体之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理解和认知,既需要对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本质进行广泛理解和深度阐释,又需要跟学科实践的具身性活动和“常识”联系在一起。对于电影研究来说,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也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及其各领域愈益加速的思想演化、学科融合与知识增长、话语迭代,除了“理论”与“学科实践”本身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容和大量增殖之外,电影也正在转变为一种或数种具有多模态、全感知和强交互特征的媒介/艺术和技术/文化形式,电影研究因此正在面临后现代与后信息双重语境下的“解构”机制与普遍的不确定性,以及更大规模和日趋严重的“围困”和“危机”。13
其实,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前,“理论”本身已经开始陷入无法自证也很难摆脱的困扰、迷惑与悖论之中。在《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14(2014)一书中,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便指出,文学理论的悖论在于理论家只能忠实于一种理论,所以最后的问题总是不能得到解决。常识乃至文学本身永远如幽灵盘桓于理论之中,而作为文学元批评话语的理论,无力得到足够有效的定论并让常识全面崩盘。因此,理论理应作为一种终极的反思而存在,并以此不断质疑自身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和文学的话语。同样,在《理论之后》15(2003)一书中,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驳斥了一度占据正统地位的文化理论。在他看来,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其黄金时期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已有几十年。雷蒙·威廉斯、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埃莱娜·西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逐渐退出了核心话语。
显然,“理论”不仅因其无法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而承受着理论本身的质疑。“电影理论”还因其徘徊在电影学、电影美学、电影符号学以至电影批评学的缝隙之间而遭到电影哲学的否定;甚至,电影史理论也只有在知识/媒介/电影考古学意义上才可以被纳入历史理论。在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学”状况之下,“理论”与“电影”总在面临抵制、怀疑、折中或者被取消的命运;而当“理论”与“电影”的拓殖和传扬、狩猎和探险,一旦进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与智能涌现普遍爆发的场景,就会真正走进以数据/算法和界面/文化为标志的“黑匣子”;随着机器崛起、屏幕扩张,“世界—屏幕”或“一切—屏幕”将会创造一种更新的时空观念和感知形式,既为“理论”自身准备了“挽歌”,也为电影研究边界的拓展和范式的革新带来了令人期待的愿景。
为了解除并克服这种因理论或电影理论而产生的“围困”和“危机”,诸多思想与文化、媒介与电影等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在试图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寻找可能的路径。其中,尤以弗朗切斯科·卡塞蒂(Francesco Casetti)与大卫·罗德维克(D. N. Rodowick)的著述为代表。
在《理论、后理论、新理论:话语的变迁与对象的嬗变》16(2007)一文里,卡塞蒂便切中肯綮地指出,过去十年间,电影理论不断受到电影史学、文化研究、美学与哲学等学科基本原则的公开挑战,所谓理论的式微,也确实为新兴范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当然,理论的相对边缘化,也折射出电影研究领域存在的困境。
首先,随着“新形态”与“新载体”的涌现,电影已不再是可供特定研究方法处理的单一恒定对象,因此,电影理论的薄弱之处,正表明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如今已呈离散状态;其次,电影始终处于众多不同领域的交汇点上,其历史是媒介史、表演艺术、视觉感知、现代主体性形式等诸多领域历史的“融合体”,电影理论的缺陷,恰恰反映出人们亟需重新审视那段从未真正统一的独特的历史;再次,在后现代语境下,任何对理性的诉求都可能沦为陷阱,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本身就抗拒任何形式的体系化归纳,这种理论困境恰恰表明,人们需要保持对该研究领域的“开放态度”。
卡塞蒂认为,正是通过对这三个关键问题的讨论,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型理论体系”的萌生:它既非正式的又呈离散状态,通过各种话语形式显现出来;这些话语形式满足于对现象进行阐释性解读,旨在更深入地理解电影本质并推动其被社会认可。
正是通过对“理论”困境和电影理论缺陷的分析,卡塞蒂才在《卢米埃尔星系:未来电影的七个关键词》17(2015)一书中表示,虽然希望有丰富的参考资料,并试着重建一些精确的系谱,但也并不提供系统的电影史;该书的目标,是要描绘一个“理论架构”让我们思考:当下的电影一方面超越了过去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忠实于原貌;电影已经转移到了一个陌生的领域,但又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其“特性”,即使这样的“特性”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之上。
相较而言,罗德维克的著述不仅把电影研究当作21世纪人文研究的主要场域,而且更具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在《电影的虚拟生命》18(2007)一书里,罗德维克提出,在与计算机屏幕的互动中,本体论是如何改变的?仿真的自动机制预示了何种与世界和集体生活的认识论及伦理学关系?而在一个由电子和数字影像主导的时代,电影研究是否仍有意义?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罗德维克探讨了电影被数字技术取代之后,摄影本体论的消逝给电影和电影研究带来的哲学后果,并将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历史当成评估新媒体最为有效的概念基础。在他看来,对于可以预见的未来,电影将继续存在、进化并经历新的转型,还将是对动态影像的审美体验和以时间为基础的形象表达进行评价的基线。也许电影会在某一天融进或加入一种新的计算机艺术的变体之中,但电影的历史与电影理论的概念仍是定义过去和当前世纪的各种新媒体以及视听性的最有效的语境。电影研究真正卓越的成就,是相比其他相关学科,已经为处理一些最紧迫和最有趣的问题建立了更多的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基础。
同样,在《理论的挽歌》19(2015)一书中,罗德维克继续延展自己在《电影的虚拟生命》中的思路,对“理论”本身的变迁展开执着探索,并致力于电影研究的学术史。他指出,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科学哲学中,都不可能赋予“理论”一个稳定的定义,使其必然导向一个可臻完善的概念,从而达成最终的共识;但一种新的“视听文化”,我们才刚刚开始辨别其广阔而不能确定的轮廓,它便召唤我们去探索一种新的存在模式和体验形式。如同任何被现代性的冲击眩晕所迷惑的灵魂,我们寻求一个“概念指南针”来指引我们回家。在罗德里克看来,这种导航设施的一个名字是“理论”,另一个名字可能是“哲学”。然而,“电影”与“理论”之间的关联并非简单、自然或不证自明,在对“理论”的“稳定的不稳定性”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罗德维克向各种“理论”的代言人发起了挑战,这与其说是为理论谱写“挽歌”,不如说为理论谱系和电影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波德维尔与卡罗尔等合编的《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开始,到波德维尔—齐泽克的“后理论”之争,再到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罗杰·库克(Roger F. Cook)、马尔特·哈格纳(Malte Hagener)、肖恩·丹森(Shane Denson)与茱莉亚·莱达(Julia Leyda)等人的“后电影”理论,以至“后人类电影”等各个层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翻译成中文公开发表和出版,并在最近一些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和电影研究领域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这也使得这些欧美学术话语中的论题,在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得到了继续延展的契机。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对“后理论”“后电影”以至“后人类电影”等所产生的热情和兴趣,既是为了应对数字时代和新媒体全面冲击下电影/媒介以及中西方学术正在面临的共同难题,又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一种对新的理论建构、思维方式与电影研究范式的追寻。
正如《闪速前进:后电影文论选》20(2023)一书“编者导言”所示,“后电影”理论有意弱化文化研究范式与形式主义范式之间的二元对立,开启立足现实、综合对话与包容开放、指向未来的重建电影研究思路和电影理论范式,但也同样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真正面对数字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形态丰富性和问题复杂性,充分提炼和总结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并加以理论化。确实,从“重建”到“重构”,电影研究尤其中国电影研究还需要继续拓展电影研究边界、革新电影研究范式与推动电影知识生产,在增进学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完成人工智能驱动的主体定位与思维跃迁。
跨界融通:以数智思维重构电影研究
为了应对“后电影”的学科实践问题并克服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在数智时代建构电影知识体系尤其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不仅需要在知识平台和人机协同的智能涌现层面完成对“重写”电影史的超越,展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电影史“重构”工程,而且需要在跨界融通的数智思维与多模态、全感知和强交互的电影思维基础上,通过拓展电影研究边界、革新电影研究范式与推动电影知识生产,增进学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完成人工智能驱动的主体定位与思维跃迁,并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整体思维观,跨越中外、古今、史论与知行的界限,在主客交互、道器并重、物我混融与人机共生的层面重构电影研究。
本文中,数智思维是指人类大脑在数字思维与智能思维深度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以及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和应用,以实现创新驱动、决策优化与能力提升的思维方式。作为开启未来世界的关键密码与核心驱动力,数智思维确乎正在改变宇宙万物以及人类自身所面对的一切,当然更包括电影、运动影像及人类正在创造并见证的视听文明。以数智思维重建电影研究,亦即以多模态、全感知与强交互的电影思维,为电影研究带来创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并以此重构数智时代的电影研究。在这里,会工作、会思考与更会融创的人工智能,将跟更具创造性、更具情感价值和更具伦理道德意识的人类智能合二为一,不仅有助于促进多元共生的电影思维,而且可以为电影知识体系奠定向善和向美的基石,更为中国自主性电影知识体系建设寻找突破的契机。
以数智思维重构电影研究,首先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并践行全球网络化思维,在线上与线下的对话交互中构建电影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电影研究领域的全球网络化思维,就是为了适应互联网与智能时代的总体趋势,强调电影研究的信息共享开放合作、跨界融通与持续创新的思维方式,通过系统的学科内涵建设、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文工融合的创新实践,打造具有艺媒能力与数智素养的知识社群,培养兼具专业深度与跨界思维的新型人才。因此,更有必要从战略性高度,在大数据与智能驱动的平台建设层面予以整体谋划和精心布局。
其次,还要在全球网络化思维之外,基于多模态、全感知与强交互的电影思维,将电影、电脑与人脑及其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和彼此映射的内在机制,从功能模拟、结构体系和信息处理方式等方面展开研讨和应用,通过世界图景的构建以及深度学习和人机交互而形成的记忆、情感与知觉、伦理,使数智时代的电影和电影研究得以跨越中外、古今、史论与知行的界限,真正获得想象的飞升与表达的自由。事实上,多模态、全感知与强交互的电影思维,不仅是电影构建世界图景的技术/文化语境,更是计算机生成知识与人类大脑理解世界的文化/技术手段,都是通过包括视觉、听觉、文本、触觉等多种感官在内的输入和输出方式,利用多种不同形式或感知渠道的信息进行表达、交流和理解、推论。21
另外,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整体思维观,通过跨越中外、古今、史论与知行的界限,在主客交互、道器并重、物我混融与人机共生的层面重构电影研究。总的来说,跟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具有整体、辩证与直觉思维特征;这种思维特征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转化与创造之中,又有了各个不同的新趋向,并凝聚成可与全球文明对话的中华智慧。其中,冯契“转识成智”的“智慧说”、李泽厚的“实践理性”说、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张世英的“万有相通”观念、王树人的“象思维”、张立文的“和合学”以及钱耕森的“大道和生学”等等,都充满着中国思想与智慧的主体意志、当代意识与蓬勃生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研究中,或可得到更进一步的借鉴与升华。
目前,基于人工智能与电影思维的跨界融通而展开的电影研究,其实刚刚起步。仅就“重构”电影研究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而言,通过对号称世界最大、全球响应、用户友好并屡获殊荣的学术平台科睿唯安(Clarivate)及其旗下的ProQuest,以及全球最大的中文数据库和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全球各大综合性学术平台中,还较少出现专业的“电影研究”版块;同样,以数智思维尤其电影思维创立和运行并主要服务于电影研究,或以电影研究为主要内容和基本导向的专业平台,在世界各国分布并不均匀,在国内也不多见;其中,有些电影研究专业平台或因数据来源存疑和知识权属不明,或因技术落后和资金短缺,往往难以为继,或重新沦为数据“孤岛”,丧失了学术平台本来应该具备的价值和意义;而真正以数智思维下的电影思维搭建电影研究的新兴平台,也就成为中外电影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此,笔者跟海内外电影与媒介研究、计算机、信息管理、人工智能以及图书馆、资料馆、档案机构、视频平台、出版社等相关部门合作,搭建了一个以电影研究和学术导向为中心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movie. yingshinet.com,CCKS)。经过多次改版和“升级”,CCKS目前是一个基于多模态大模型技术,通过权威电影史料数据集和电影知识专家系统而构建的中国电影数字基础设施,也是一个以高质量数据驱动、自主性知识体系为目标,深度融合教学创新、艺术创作、科研攻关与产业转化、社会服务等多元维度,践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体。另外,CCKS以影人年谱、电影计量、电影百科、藏品索引和数字生命等五个板块为主架构多模态混合专家模型(MoE),结合自主开发的汉字统一OCR平台(CTOP)、电影计量工具(CCKS-Cinemetrics)和梦蝶心智模型(郑正秋数字生命),在学术导向、优特数据、众包群智和开源共享基础上,展现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不断融合创新的愿景,也试图为重构电影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反思或批判的中国方案。
注释:
1 Susan Hayward. Cinem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12. 中文译本信息:[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第三版).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Annette Kuhn, Guy Westwell. A Dictionary of Film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2.
3 Jill Nelmes.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2.(中文译本信息:[美]吉尔·内尔姆斯,编.电影研究导论(插图第4版).李小刚,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4 Division of Cinema & Media Studies. [2025-06-03]. https://cinema.usc.edu/mediastudies/index.cfm.
5 Film and Media Studies. [2025-06-02]. https://apply.jhu.edu/academics/majorsminors-programs/film-and-media-studies.
6 David Bordwell, Nöel Carroll, eds. Post 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2012.(中文译本信息:[美]鲍德韦尔,[美]卡罗尔,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柏敬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11.)
7 李道新.数字时代中国电影研究的主要趋势与拓展路径.电影艺术,2020(1):21-29.
8 李道新.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新路径.电影艺术,2020(5):27-35.
9 李道新.银幕的在场与生命的庄严——媒介更迭时代重析电影本体的理论尝试.艺术学研究,2022(6):57-65.
10 李道新.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3.
11 李道新.电影史三体.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
12 参见:[法]阿兰·巴迪欧.电影作为哲学实验.李洋,译.[法]米歇尔·福柯等.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李洋,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1-53.
13 Robert Sinnerbrink. Sea-Change: Transforming the“Crisis” in Film Theory. NECSU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2012,1(1): 67-84.
14 Antoine Compagnon. 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Littérature et sens commun. Editions du Seuil: Média Diffusion, 2014.[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 Theory. London: Allen Lane, 2003. 中译本信息:[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6 Francesco Casetti. Theory, Post-theory, Neo-theories: Changes in Discourses, Changes in Objects. Cinémas, 2007, 17(2):33-45.
17 Francesco Casetti. The Lumiere Galaxy: Seven Key Words for the Cinema to Co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文译本信息:[意]法兰西斯科·卡塞提.卢米埃星系:未来电影的七个关键词.陈儒修,译.台北:一人出版社,2021.(本文中译为弗朗切斯科·卡塞蒂)
18 David Norman Rodowick. The Virtual Life of Fil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文译本信息:[美]D.N.罗德维克.电影的虚拟生命.华明,华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86-202.
19 David Norman Rodowick. Elegy for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荷]帕特里夏·皮斯特斯等.闪速前进:后电影文论选.陈瑜,编.陈瑜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5-38.
21 早在2004年,计算机与神经科学家杰夫·霍金斯就通过对大脑皮层体系的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从计算机到人类大脑再到智能机器的框架。在他看来,大脑皮层体系通过其嵌套结构建立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模型(层级结构模型)。〔参见:Jeff Hawkins, Sandra Blackslee. On Intelligence. New York: Macmillan, 2004.(中文译本信息:[美]杰夫·霍金斯,桑德拉·布拉克斯莉.智能时代.李蓝,刘知远,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123.)〕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栏目导航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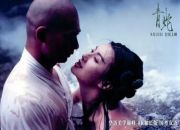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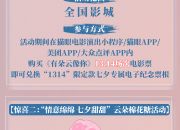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2号